父親因常年工作在外,在家的日子不多,所以我們難得和他相聚一起。兄弟姊妹七人中,四明和方芬對他尤其感到陌生。文革前後,老四因他而受過不少折磨。為了瞭解自己的身世,近年來他不斷閱讀有關材料丶上網查看丶實地追蹤,終於有了成績,明白父親的為人。如今大姊桂芬卧病在床,不能言語:大哥偉明英年早逝,能夠幫忙老四添磚加瓦的,恐怕是捨我其誰了。
(一)竹山村
兒時生活在竹山村,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。可不是嗎?日日像野孩子般,不必洗臉刷牙,不必上課,無需要穿衣服,又可以隨處大小便。有人問我的祖母,人稱四婆的;「四婆,你有幾多孫仔孫女呀!」答曰:「我唔知道噃。你到村口行吓,見到冇著衫嘅,就係我嘅孫仔,挽著半邊褲嘅,就係我嘅孫女喇。」


村裡娶媳婦,慣例有「打閣」一項。新郎迎娶,陪伴人等必帶備長竹竿,以防女家迎面而來的石塊。「打閣」就在我家旁邊的小巷進行。一下子噼里叭啦,好不熱鬧。女方居高臨下,駐紮在小巷的上頭丶我祖母居室的旁邊。她們擲石的功夫到家,男方的竹竿陣招架不住,又不能投降退縮,只好哀求大妗婆說項。但要達成和議,大封利市是少不了的。
我家另一邊是上間。那是婚禮拜堂和初生男嬰,上燈的地方。有次看見人家拜堂,便稱自己怎樣坐在上間的門檻上,看見父親拜堂的經過。這自然成為全村人的笑柄,可我還是堅持己見,絕不改口。這種愚而好自用,包頂頸的性格,到老不曾有變。
村裡孩子既終日無所事事,遊手好閒,不旋踵便沾染惡習。我大哥十二三歲即沉迷賭博。消息傳到父親耳中,於是著人把他帶到韶關十二集團軍總部。到達後,父親沒有立刻叫他讀書,乃請副官陪他游泳丶騎馬和打獵。過了一段日子,等到大哥玩得開心,開始有點疲累,父親才勸導他上學。後來大哥是帶著槍枝和馬匹回村的。那時在村裡游泳,全都是狗仔式,游得不快,也不遠。一天西水大,大哥竟從門樓對下,以自由式一直游到公路那邊的文筆,令眾人大開眼界。隨後大姊攜同大哥往別縣上學˙,游泳絕技遂由堂兄五謙繼承。他是第二位由村子游到文筆的健兒,同時也成為我們眾小嘍囉的頭目。
父親任職四會縣長,正值抗日高峰期。我初到縣府,首先學習的,便是洗臉刷牙,穿衣著鞋和上廁所。頭一天,工人稱呼我為「二官」。我四顧左右,茫然不知所措。
縣府對開馬路有不少露天防空洞。敵機來時,我們都躲在洞裡。有時眼見炸彈從頭頂飄搖而過,嗚嗚作響,令人心驚膽跳。
四會多竹,竹林常有老虎出沒。晚間虎嘯一起,婦女便拿起竹桿排開陣勢,男人則躲在後面,或抽煙,或抱孩童,若無其事。
後來我們利用竹在一個水塘邊蓋了一座樓房。父親百務纏身還不忘抽空教我們讀書寫字。他用階磚刻上自己寫下的大字,叫我和三弟廣明照著臨摹。可惜我們都不是材料,無法學得父親的一二。
有次讀到水獺,我硬是將獺讀為賴。父親沒有我辦法,只好說,多聽多聞是有益的。
俄而二妹會芬出生,臉色紅潤,人見人愛。一家大事慶祝,卻忘記邀請欖塘的一位親戚,致令祖母大發雷霆,父親怎樣賠罪,都無濟於事,場面尷尬得很。
有次婦女節,邀請縣長夫人致詞。幸好大姊早有準備,詞理清新動聽,獲得一致好評。
近聖里三號的居所原來是一間當舖,父親買入後加以大幅改變。在這裡我們和父母相處了一段較長的日子。同樣地,父親經常指導我們學習,尤其費神修改我們的文字。有一次,我所寫的被改得一塌胡塗,心中有氣,竟脫口而出:「好呀,我中文不行,以後我就用英文寫給你看!」不久我來香港,才知道自己連英文26個字母的發音也不準確。
和父親通信,每次總見他把信修改後寄回來,一直到我上大學時還是那樣。上世紀七十年代,我再次踏足大陸,和大姊談及,她也有同樣的體會。在台北,聽他說寫文章要精簡,我問他如何做到。他於是舉了個例子。
「有一匹馬被圈在圍欄裡,時間長了,性情愈益暴躁,屢思逃走。看馬人終於疏忽一時,給它跑掉。馬匹沿大路飛奔,一個途人不幸給撞倒,死了。」
這段文字古人是怎樣說的呢? 很簡單:「逸馬斃人於途。」
1949年初,基於內戰迫近廣州,父親著大姊丶大哥和我先到香港躲避一下。我於是向真姑寫信,告訴她我們的情況。上午擬了個草稿,拿去郵局一問,郵資金圓券壹佰萬元。下午我謄好了信,再到郵局,索資壹佰五十萬,而且不給郵票。金圓券由1948年8月開始發行,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,只使用了十個月左右,貶值卻超過二萬倍。人們稱之為「濕柴」,寧願撕開港幣壹圓當兩個五毫用,或以貨易貨,也不用金圓券。
(四)香港
唯一的問題是我往那裡去找學校?以肇中的水平,我肯定無法入學。咋辦?真姑的好友老惠貞姑娘是聖保羅男女中學的總務,憑她的安排,從後門溜了進去。可是畢業那年,我卻是堂堂正正從正門走出來的。
畢業了中央那個是我
廣州解放,同年10月,大姊大哥乘第一班火車返回廣州,留下我一人在外面。
(五)台北
1952年10月,我初次來台,那時父親住在長安東路一段24號,而蔣經國是在18號。日治期間,這一帶原是日本高級官員的豪華住宅區。房子建築是日式平房,環境優雅;房子裡面有日式露天小花園,假山流水潺潺,矮松蒼勁挺拔。父親許多文章,想是坐在廳中,眼望花園,有感而發。

台南工學院1954

台南工學院1954
我就讀台南省立工學院化學工程系。這原是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,是日人南侵培訓技術人員的基地。1956年改制為台湾省立成功大學。我適逢其會,成為成大第二屆畢業生。畢業後我自願留台一年,協助美國軍中牧師李達道(Donald Lee)在成大附近開辦學生中心及創立教會,稱之為「善牧堂」。1989年,元基中學畢業,正愁何處升學。李牧相隔三十年突然攜第二任妻子Margaret Lee及一雙兒女來訪。Margaret 時任Oakton Community College 的副校長兼教務長。真是喜從天降,一拍即合。
寒暑二假,尤其是寒假,我都會返台北探親。 頭幾年,父親總喜歡帶著我到張昭芹家裡拜年。張乃前清舉人,歷任要津,颇有政聲;道德、文章均為世範;擅書法,精小楷。遷居台湾省後,與于右任、贾景德領導詩壇,稱為詩壇三老。父親敬重張氏,尤其是因為他是第七戰區中将秘書長,同屬余漢謀麾下。張氏的公子張茲闓,當過經濟部長、台灣銀行董事長;女兒張婉度是錢思亮的原配。錢的兩個兒子,一個當過財政部長,叫錢純;另一個當過外交部長、監察院長,叫錢復。 同一時間,余伯泉(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碩士,留英期間曾獲燕拿法院大律師資格。回國後,投身軍旅,歷任陸軍軍職,累升至軍長「1961年」、副參謀總長「1965年」、總統府參軍長「1966年」」、三軍大學校長「1968年」等職)也攜兒子國藩(芝加哥大學宗教與文學雙博士。1983年,余國藩發表四巨冊英譯「西遊記」,這是西方世界首部「西遊記」全套英譯本,轟動一時)到來。看來這儼如余漢謀僚屬及家眷一年一度的大聚會。我和錢復國藩雖有交談,但始終覺得有些隔閡。所以後來也向父親暗示自己不願意參加這樣的盛會。
寒暑二假,尤其是寒假,我都會返台北探親。 頭幾年,父親總喜歡帶著我到張昭芹家裡拜年。張乃前清舉人,歷任要津,颇有政聲;道德、文章均為世範;擅書法,精小楷。遷居台湾省後,與于右任、贾景德領導詩壇,稱為詩壇三老。父親敬重張氏,尤其是因為他是第七戰區中将秘書長,同屬余漢謀麾下。張氏的公子張茲闓,當過經濟部長、台灣銀行董事長;女兒張婉度是錢思亮的原配。錢的兩個兒子,一個當過財政部長,叫錢純;另一個當過外交部長、監察院長,叫錢復。 同一時間,余伯泉(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碩士,留英期間曾獲燕拿法院大律師資格。回國後,投身軍旅,歷任陸軍軍職,累升至軍長「1961年」、副參謀總長「1965年」、總統府參軍長「1966年」」、三軍大學校長「1968年」等職)也攜兒子國藩(芝加哥大學宗教與文學雙博士。1983年,余國藩發表四巨冊英譯「西遊記」,這是西方世界首部「西遊記」全套英譯本,轟動一時)到來。看來這儼如余漢謀僚屬及家眷一年一度的大聚會。我和錢復國藩雖有交談,但始終覺得有些隔閡。所以後來也向父親暗示自己不願意參加這樣的盛會。
到北投奇巖路余公館,我倒是十分歡喜。余漢謀伯伯性情慈祥,對小輩不擺架子。還有,過年 到公館吃肇慶裹蒸糉另有一番滋味。就是在內戰打得不可開交期間,余公館仍有辦法從肇慶取得西江兩岸特有的冬葉、水草。蘇如師傅從韶關跟隨余伯伯到台灣。他巧手妙製的裹蒸糉別出心裁,不呈埃及金字塔形,而是正方形。也不知蒸製了多少個小時,總之到了年卅晚午夜十二時正,打開大蒸籠,人人眼前一亮,偌大的裹蒸糉香味撲鼻,入口鬆化。到我結婚後,同月明來台,還能品嚐這種極品。後來公館減縮人手,蘇師傅去台北開大飯店,客似雲來。
我們在余公館山下蓋了一處四家村,分別由我,蘇師傅,,歐副官及余二太的姪女入住。二太是肇慶人,大方,不拘小節。暑假我來四家村,二太經常會叫我和她的姪女上陽明山游泳。陽明山游泳池的水是山溪水,雖天氣不差,可水溫仍低。她兩人身廣體胖,有脂肪層保護;我就要捨命陪君子,真是有苦自家知。我離開台灣後,四家村由堂兄操明進駐。 

鄉親梁寒操處,有時我也去串門。梁伯伯謙謙君子,對小輩愛護有加。我結婚時還給我送來對聯。
為了求學和工作,我離開了台灣。這時父親也從長安東搬到南京東的自置房子。不幸的事終於發生。事緣有一再婚女士給丈夫毆打,父親作為律師予以調停。事後這李姓女士來到南京東的住宅不肯離去。父親的誼弟劉鍚誥警察局長勸說、驅趕,想盡辦法,全屬徒然。無奈,只好由得她。 1964年我出國前與月明到台灣辭行,父親一再向我說明,他們是分房而睡,絕無肌膚之親。既然同居,父親希望李氏好自為之,介紹她唸佛,給她改名為美賢,說我們可以稱呼她為姨媽。1969年,我們從德國回來,他們搬到中央新村,據說已經結婚。我從旁觀看,發現父親有莫大的委屈。1981年9月,我赴美加,路經台北,於是請姨媽陪我去掃墓。她帶我到立法院直接找倪文亞。倪院長以為我在找工作。姨媽急忙說是要車子。司機開車來了,載我們到南港墓園。路上她忽然跟司機談中央新村的一些奇聞。她說:「唉,中央新村有許多"劫收黨",駭人聽聞。」司機說:「願聞其詳。」「可不是嗎?中央新村的委員年紀大了。很多人老年失伴,要不就是兒女都在國外,留下孤家寡人。一些年輕的姑娘乘虛而入,硬是說仰慕老先生的道德文章,願隨侍在側,白白奉獻。」「老先生操勞一生,為國為民,到頭來獨守弧燈,怎不難過?」「如今聞到青春氣息,又如何抗拒?」「最後雙眼一閉,財物就轉手了。」姨媽滔滔不絕,司機頻頻點頭。我默不作聲,心裡有數,因為她的所為,正如她說別人一樣。好精彩的自白啊!
為了求學和工作,我離開了台灣。這時父親也從長安東搬到南京東的自置房子。不幸的事終於發生。事緣有一再婚女士給丈夫毆打,父親作為律師予以調停。事後這李姓女士來到南京東的住宅不肯離去。父親的誼弟劉鍚誥警察局長勸說、驅趕,想盡辦法,全屬徒然。無奈,只好由得她。 1964年我出國前與月明到台灣辭行,父親一再向我說明,他們是分房而睡,絕無肌膚之親。既然同居,父親希望李氏好自為之,介紹她唸佛,給她改名為美賢,說我們可以稱呼她為姨媽。1969年,我們從德國回來,他們搬到中央新村,據說已經結婚。我從旁觀看,發現父親有莫大的委屈。1981年9月,我赴美加,路經台北,於是請姨媽陪我去掃墓。她帶我到立法院直接找倪文亞。倪院長以為我在找工作。姨媽急忙說是要車子。司機開車來了,載我們到南港墓園。路上她忽然跟司機談中央新村的一些奇聞。她說:「唉,中央新村有許多"劫收黨",駭人聽聞。」司機說:「願聞其詳。」「可不是嗎?中央新村的委員年紀大了。很多人老年失伴,要不就是兒女都在國外,留下孤家寡人。一些年輕的姑娘乘虛而入,硬是說仰慕老先生的道德文章,願隨侍在側,白白奉獻。」「老先生操勞一生,為國為民,到頭來獨守弧燈,怎不難過?」「如今聞到青春氣息,又如何抗拒?」「最後雙眼一閉,財物就轉手了。」姨媽滔滔不絕,司機頻頻點頭。我默不作聲,心裡有數,因為她的所為,正如她說別人一樣。好精彩的自白啊!
其實父親是頗愛熱鬧的。無奈兒女都不在身邊,最後連我這隻小鳥也飛走了,卻日日要面對一個語無倫次,嘮嘮叨叨,話不投機,卻又自以為是的人,能不倍惑淒涼?真的,我離去的時候,他要我找另一隻小鳥回來。可我又有甚麼辦法?
1956 成功大學
1956 成功大學
記得我結婚後,帶同月明來台,他高興到不得了。一面吩咐姨媽領我們到處玩耍;一面親自陪我們南下。等到我們說要遊蘇花公路,請他留步。我立刻知道說瞎話了。因為他頓然呆了,說,好好,你們自己去玩罷!
1964
1969年,我們從德國回來,在台灣呆了一個月,他馬上精神煥發,陪我們南下高雄台南等地,興盡而返。可惜這樣的日子不多了。1973年7月,我接到四叔電話,說父親危在旦夕,必須立刻來台。我趕到台大醫院,看見父親仍在昏迷中。我在床沿等了一個多小時,父親悠然張開雙眼,示意我走近,對我說:「姨媽有千般不是,到底我身邊還有個影子。東西隨她拿罷。」我說會來看他。他說:「能嗎?」再也不說話了。
1969年,我們從德國回來,在台灣呆了一個月,他馬上精神煥發,陪我們南下高雄台南等地,興盡而返。可惜這樣的日子不多了。1973年7月,我接到四叔電話,說父親危在旦夕,必須立刻來台。我趕到台大醫院,看見父親仍在昏迷中。我在床沿等了一個多小時,父親悠然張開雙眼,示意我走近,對我說:「姨媽有千般不是,到底我身邊還有個影子。東西隨她拿罷。」我說會來看他。他說:「能嗎?」再也不說話了。
台南 我協助建立的台南學生中心 1969
来源:smtang135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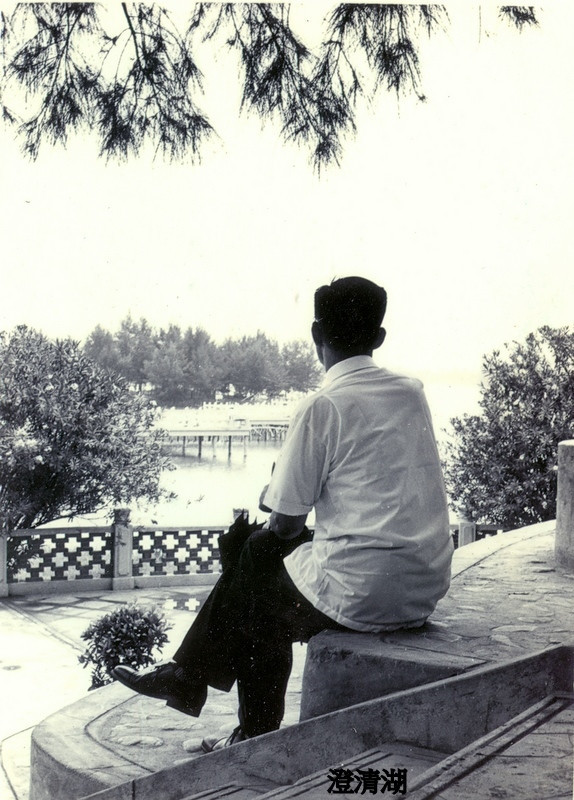


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